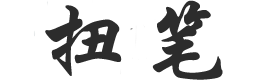县域城镇化的底层逻辑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城市、大城市与都市圈,是以和平与发展为第一主题,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集聚效应的服务业快速崛起,全球化高歌猛进背景下的产物。当这一切发生变化,当城市尤其是超级大城市在疫情和变局中变得无比脆弱的时候,国家意志可能需要重新从乡土中国中寻找安全感和归宿感。
大城市和都市圈,是发达文明社会的象征。她代表着更广泛的分工合作,更大规模的思想知识集聚,以及更加开放包容的市民心态。这些超级大都市,往往都是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在以知识经济、技术创新、信息网络为主导的产业范式下,大城市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优势。城市化的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接近70%的时候,超级大城市崛起是必然的事情。202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5%。
当然,超级大城市也意味着一项挑战。在这里尚且不说倍受争议的资源消耗和环保问题,我们关心的是这些超级城市的管理和治理。一方面,对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着与以前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复杂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对城市居民来说,面临着从村民、工人向市民的身份转换。如果说在过去的乡村和大工厂时代,人们以血缘、村落和工厂为集体型身份认定,那么在大城市里面,市民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体,市民身份的定义和功能需要经历足够长的适应时间。很简单,城市是陌生人的集聚,熟人社会的乡绅治理和无讼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必须以法制作为前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底层上改变了中国已有的,以空间扩张和“基建—土地—债务”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尤其是以全球化、国际化和数字资本扩张为时代主题的超级大城市。国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对无序资本和房地产债务的治理,实际上表达的也是对这种可能失去控制的超级城市化的忧虑和不满。而爆发自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又进一步加速了大城市化的解构。人们突然发现,当奥密克戎谱系病毒来袭,对一个超级大城市的静态管理是无比困难的。即使能以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了管控,但又面临着种种与市民社会、法制社会相矛盾的地方。人们在此时感受到了在大城市弥漫的脆弱、焦虑与迷茫。
而站在国家意志的高度,在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剧变的形势下,可能考虑的并非仅仅是如何让城市变得更精致,更法制化和现代化,而是一个安全稳定和持续生存的问题。如果基于这种考虑,就必须放弃代表发达文明社会方向的大城市化,重新将目光和资源转向广大农村和县城。因为在这片更加广袤的乡土中国大地上,生活生产可能变得相对粗糙了一些,但是能源、资源和粮食有了基本的保障。如果说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大量农民放下手中的“饭碗”轻装进城,那么在变局与安全的新主题下,新的上山下乡活动可能并非仅仅是历史的轮回。国家必须从下沉的城镇化甚至是去大城市化中,寻找新时代赖以发展和生存的根基。或者,构建新的缓冲地带。
从极端的国家安全情形来看,超级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大城市,就像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这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全国的内循环系统就遇到了阻梗。如果回想上世纪60年代的西南新三线建设,就会理解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城市化布局。也应该看到,西南地区之所以后来能涌现出众多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城,也并非是偶然。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产业与供应链的“去中心化”分散布局,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安全稳定的考虑外,还可以通过产业化带动新的城镇化,解决县域城镇在大城市化过程中被虹吸人口和资源的问题。然而,这里面有个规律需要在县域城镇化中对抗,那就是第三产业或现代服务业的崛起,本身是需要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县域城镇的产业化,比较优势是重工业、高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以及工业化的农业等。因此,这意味着重新向重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回归。然而乡镇企业能否再度崛起,以形成县域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我们还需要观察。
第二个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和资源再配置问题。如果城市化的主战场一味定格在大城市,资源和人口一味向超级城市集中,那么这些城市需要谁来供养?乡村振兴的战略半径是不是距离资源和政策中心过于遥远?扑身于农村的年轻人才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解决?他们更高品质的生活追求(比如喝一杯星巴克咖啡,看一场话剧等)如何满足?更高的创新思想和精神交流活动如何实现?城市更加靠近乡村,那么人才也就会更愿意长期留在乡村,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否则投身于乡土的年轻人总是遥望城市。县域城镇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
第三个可能比较迫切,就是大变局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如果说在全球化崛起的年代,中国依靠廉价的全球粮食市场,让数亿农民和大学生从乡村土地涌入工厂、工地和城市办公楼的时候,那么在去全球化、贸易脱钩、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城市还能不能以低廉的粮食成本养活和承载这么多的人口,就需要引起高层决策者的思考。尤其是,俄乌冲突还在发酵,乌克兰是世界大粮仓,粮价今天在疯狂上涨。而美国、巴西等国作为中国主要的粮食进口国,又受制于国际政治格局大环境,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供给短缺。“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固然是一种源自传统封闭和对抗时代的思维和焦虑,但是在复杂的大变局大乱局背景下,也是国家一种本能反应。要保证粮食安全,要养活八亿城市不事农业劳作的人口,必须走农业工业化道路。县域城镇化会更加靠近土地和粮食,缩短了从城市向农地的资源配置距离。
大城市的就业饱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年轻人需要重新从乡土中国中寻找实现价值的机会。当然,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规律,大城市的超级规模效应和网络涌现效应,第三产业、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消费型社会的崛起,都大大增加了大城市的就业机会。然而,当前中国正在对互联网平台、大金融产业、房地产债务、传媒娱乐等进行严格的治理。这些行业因此在大幅裁员,同时又有一千多万的应届毕业生。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又严重不足,不会大幅度投资和招聘。可以说,大城市已经无法承载这么多的年轻人,那么他们将向何处去?通过新上山下乡运动推动县域城镇化,广阔天地、大有所为。县城成为就业蓄水池的“湿地”,或危机的缓冲地带。
最终的逻辑需要归结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与管理一个复杂的大城市相比,管理一个小规模的县城可能相对简单,减少了管理者的制度变迁和人才压力。大城市固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运营成本,通过知识集聚中的外溢效应提高市民素质,但是可能并不能匹配公共治理者的认知结构——城市大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提高社会治理、自治理、第三方治理的能力。当大城市的复杂治理需求越来越高,但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及产品的供给跟不上时,那么城市化的下沉就不可避免。而疫情的发生加速了这一切的变化。很显然,封控、隔离等静态管理措施,在一个县城实施要比大城市容易的多。
【西泽研究院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是提供个人分享的知识,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人观点。如有侵权,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