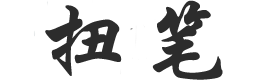言论自由在大学意味着什么?

现在想象一场关于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的课堂讨论,一些学生将死亡归因于警察的种族主义态度,另一名学生反驳了这一说法,称更有可能的解释是黑人的暴力犯罪率更高。“现在,那是特别不文明!” 教授回答。另一个学生站了起来,好像对他同学的反驳感到厌恶地冲了出去。教授一拍桌子,叫道:“坐下!” 当他试图重新控制房间时。
在怀特广场——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言论自由区——一个学生团体摆出一张桌子来支持一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诽谤者试图窃取该组织的标志,促使支持者拍摄标志窃取者和双方随之而来的嘲讽。
对于大学应该如何解决学生感到受到攻击或沉默的冲突(有时双方同时感到),没有简单的答案,正如哲学家兼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黛布拉萨茨所说,“大学的一个中心目标——创造知识——取决于思想的自由交流。” 但是,Satz说,她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她的观点,“教室不是街角:如果不遵守文明和相互尊重的规范,任何教室都不能成为学习的地方。”
几年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一直在争论大学校园内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到胁迫——如果是,如何以及如何应对。在这里,您将阅读四位高级教员对此事的看法,以及斯坦福大学如何培养公开对话,同时注意塑造我们教育体验的另一种大学价值观:包容。我们希望您能考虑他们的观点,然后分享您自己的观点。
Jill Patton , ’03, MA ’04,是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编辑。

当沉默不是金
拉尔夫 ·理查德·班克斯
“言语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始终谨慎选择它们。”
这是我让我的法学院学生为讨论有争议和两极分化的话题——堕胎、同性婚姻、死刑、平权行动——做准备的方式。我担心审查自己或他人的倾向可能会剥夺我们所有人对此类话题进行充分而丰富的探究的权利。我也知道,当我们讨论新政期间工资和工时法的无效时,学生们可能会以一种他们不会的方式感受到对这些话题的投入,被他们所牵连。课堂上很容易达到一种没有成效的平衡,一些学生不说话以避免受到指责的风险,而另一些学生则自信地宣称某些观点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则是偏执的。
如果学生感到受到攻击或觉得自己不属于斯坦福大学,他们就不太可能做出有用的智力贡献。
同性恋学生可能会觉得,对同性婚姻的批评意味着对他们的拒绝,这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学生可能不愿表达对同性婚姻的宗教反对,害怕受到同学的道德谴责。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来自少数族裔群体的学生可能会觉得他们作为斯坦福学生的地位受到质疑。反过来,同学们可能暗示他们不属于或拒绝提出有关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的智慧和影响的重要问题。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让其他人放松下来。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试图广泛地构建讨论框架,并围绕政策而不是人展开讨论。例如,我将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置于大学偏离严格的成绩和考试成绩录取标准的许多方面,我将同性婚姻置于关于婚姻角色和性质变化的更广泛对话中。对于这两个主题,我试图通过鼓励学生找出人们可能反对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或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的授权的明确理由来创造对话空间。
虽然围绕此类敏感问题进行对话的挑战由来已久,但我的感觉是近年来它们变得更加令人生畏,维持一个让所有学生都能自由分享观点并共同努力解决道德上令人担忧和政治上存在分歧的问题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破坏了大学校园的辩论,一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交媒体作为年轻人与他人交往和了解社会的一种方式的主导地位。现在,课堂内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课堂外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课堂上,评论几乎可以立即向全世界公开。社交媒体暴徒似乎无情无情。第二个因素与学生愿意攻击那些表达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情绪的人有关,这种倾向的一部分源于焦虑和不安全感;寻求安慰的学生寻求确定性——意识形态的安全空间。这种力量的汇合会导致令人不安的课堂动态,
事实上,最近的榜样——教师——往往不太擅长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一事实使情况变得更糟。正如学生不想被同学问责一样,教职员工也不希望因为说了一些据称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言论而成为学生的目标。教职员工经常理性地退出有争议的讨论怕被骂的问题。教员们意识到,如果确实出现问题,该机构更有可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即避免争议、抗议和不良宣传,而不是采取有原则的立场来支持教员。难怪学生们没有达到我们对全面而激烈的辩论的期望;教师也经常这样做。
我有自己的方式来反击压制辩论的力量,我强调,事实上,即使是两极分化、政治上分裂的问题也很复杂;它们突出了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难题,以及答案不明显的领域。那么,我们会做得很好,抵制自以为是的冲动,而是拥抱谦逊感,充分意识到我们自己理解的局限性。好奇心会带来比确定性更多的洞察力。
面对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我们需要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耐心。我们应该不太可能生气,不太可能指责有病。我们需要仁慈地解释他人的观点,并牢记他们可能在批评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我们;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身份,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让其他人放松下来。如果我们让他们松懈,希望他们也会让我们松懈,这会给每个人更多的空间,让他们一起努力弄清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复杂而可怕的世界。
拉尔夫·理查德·班克斯 (Ralph Richard Banks),’87,文学硕士 ’87,是斯坦福法学院杰克逊·伊莱·雷诺兹 (Jackson Eli Reynolds) 法学教授 。他的奖学金侧重于 种族、教育、就业和家庭方面的法律。

学术价值第一
通过 迈克尔·麦康奈尔
校园言论自由变得前所未有的有争议。最近一项针对2,225名大学生的全国调查发现,57%的人认为大学管理者应该能够限制被视为伤害或冒犯他人的政治观点。即使在斯坦福大学,学生们也经常呼吁大学让其他学生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的观点让他们感到不舒服,这使得认真讨论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几乎不可能。持保守派观点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不敢在课堂上或公共场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是数百万美国人所认同的主流、合理的观点,因为他们害怕招来同学的谩骂和偶尔的反对,来自少数意识形态不容忍的教师,他们只是自我审查;他们闭嘴。
在法律、政治学、历史、人文甚至医学等学科,政治异议的压制具有毁灭性的后果。大学的目的是通过不懈地运用理性和证据来寻找真相;如果压制不同意见或避免可能引起争议的调查渠道,则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在个人层面上,这当然对感到被排斥和不受欢迎的政治少数派不利,但最大的受害者是政治多数派的成员,左翼进步的学生,他们被剥夺了检验反对相反观点的论点、学习如何与另一方的人打交道的机会,甚至被剥夺了机会,有时,发现他们错了或被误导了。大学不应该是泡沫。大学教育应该让学生准备好迎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多样性和争议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遵循关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左派进步观念。
大学不应该是泡沫。
持部分而非全部观点的温和派学生可能是最危险的,在这些高度两极分化的时代,倾向于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或宗教传统主义者的学生可以找到朋友和盟友——至少在课堂之外或更多的公共场所进行讨论。但温和派无家可归。如果他们背离了左派进步的正统观念,但他们可能不希望与右派共同努力,他们就会受到谴责,我的感觉是温和的声音正在从校园辩论中消失。
斯坦福作为一所大学应该以一种超越政府应有角色的方式积极鼓励意见的多样性,我们不应满足于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应该将健康的多元化观点视为教学的必要条件。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三个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对校园环境进行调查,以确定对不同意见的表达究竟有多大的限制。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学生会感到沉默吗?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会与不同观点的人互动吗?是否正在进行严肃的跨意识形态对话?课堂是自由探究和讨论的地方,而不是思想灌输或整合的地方吗?这些必须是问题,而不是假设。作为一所注重实证的科学机构,当斯坦福认真对待校园问题时,无论是性侵犯还是高昂的住房成本,第一步都是对学生和教职工进行调查,以了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其次,我们需要提升斯坦福社区内自由交流思想的话题。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教育工作者可以假设言论自由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是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价值观。这不能再假设了。也许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言论自由在履行这一作用中的核心地位,可以成为新生入学指导的一部分。去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选择了基思·惠廷顿教授的《畅所欲言:为什么大学必须捍卫言论自由》作为所有新生都会一起阅读和讨论的书,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类似的事情。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致力于保护探究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学行政办公室,目前,当学生的海报被宿舍官员取下或教授要求意识形态一致时,学生没有明显的补救途径。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法律约束。这是一种学术价值。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赋予它生命。
Michael McConnell 是 Richard and Frances Mallery法学教授和宪法法律中心主任,同时也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聆听与学习
通过 淡褐色玫瑰马库斯
我们有两只耳朵和一张嘴;以这些比例使用它们是明智的,这种智慧归功于跨越时间和大陆的多个建议提供者,凸显了倾听的力量被低估了。
为了在斯坦福为学习、成长和社区提供稳定的基础,我们的自由表达和包容价值观应该同样强大。目前,享有使用嘴巴特权的言论自由要强大得多。包容,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没有人应该觉得自己是别人家里的客人,可以使用支持。在房屋和宿舍以及课堂上培养耳朵的使用是加强包容性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名研究文化的心理学家,我知道在制度上强调言论自由和包容之间的不平衡并不是斯坦福大学独有的。在美国,个人被理解为稳定、独立的实体,言论自由具有历史先例和广泛的哲学和道德支持的优势。人们通过谈话表达自己的权利和个性;他们影响他们的世界。美国人不断被劝告去寻找和使用他们的声音。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法律专家告诉我们,应对任何过度言论自由的最佳方法是增加言论。
当一个班级成为一个社区时,每个人都会学到更多。
包容性是一个更新、更复杂的问题,历史和制度基础要少得多。包容是困难的,因为它消除了人们对自由和独立个人的关注,而是阐明了相互依存、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后果。对构成斯坦福大学的许多经验和观点进行有意义的认可和包容是一项挑战,需要许多小的调整,以及规范、政策和实践方面的更大变化。
在我的文化心理学课上畅所欲言,我注意到在美国,谈话很有价值,因为“吱吱作响的轮子得到了润滑脂”。几名东亚背景的学生似乎不解,并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观点:“嘴是不幸的源头”和“嘎嘎叫最大声的鸭子会被枪杀”。对于那些来自世界的人来说,在这些世界中,个人不是中心化和分离的,而是被理解为灵活的、忠诚的,由与亲密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说话需要注意一个人说话的后果。研究证实,虽然对于欧裔美国人来说谈话有助于思考是真的,但对于许多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来说,谈话实际上会妨碍思考。
在课堂上,一些具有欧美背景的学生在畅所欲言和经常发言方面训练有素。正如一位学生告诉我的那样,“在我听到自己说出来之前,我什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然而,其他人,通常是那些财富和特权较少的人,或者那些第一代人,显然更加沉默寡言。一位在农村社区长大的学生,在那里他练习融入、低头和注意权威,他问我,“所有那些总是说话的学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和意见?”
当我听取这些学生的意见时,我了解到他们都可以做出很多贡献,但是按照目前的安排,与其他人相比,容易说话的人更有可能融入大学。包容性设计提出了许多与演讲相关的问题:人们是否同样熟悉和练习演讲以及在思想市场中参与积极辩论?他们觉得自己有同等的发言权和发言权吗?演讲是影响世界的最重要方式吗?我的言论何时会伤害、威胁或排斥他人?我有责任关心这个吗?
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但斯坦福大学在为包容性未来设计自身时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聆听斯坦福丰富的观点来回答。我与91年助理副教务长兼包容性和多元化教育执行主任 Dereca Blackmon一起教授的名为“群际沟通”的课程有助于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之间的交谈和倾听。基于一种被称为鱼缸的技术,学生们将自己分成小组并互相提问和回答问题,这些群体可以基于任何社会区别——专业、地区、出生顺序、宗教等。
课程通常从性别开始,学生分为男性、女性和性别不合格者。每个小组为其他小组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其他小组轮流坐在房间中央,而其他小组则提出他们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学生们根据种族和族裔、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性取向分成不同的小组,在每个单元之后,全班一起汇报,在课堂之外,学生与来自不同社会类别的学生进行讨论。
一套规范指导讨论,包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离开这里,在这里听到的东西留在这里,腾出空间,占用空间,理解你的意图并拥有你的影响。问题是真实的。男人如何成为女人的盟友?男人怎么看待约他们出去的女人?您经历过哪些微攻击?当你知道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时,你感觉如何?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你的专业?作为本地人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没有来回。重点是听。答案揭示了重要且通常不可见的差异,以及梦境和忧虑的许多相似之处。
作为这个教学团队的一员五年后,我知道倾听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一套基于对许多问题通常有多个正确答案的理解的价值观和技能。是的,这是一门致力于交流的课程,但是无论主题是什么,花时间建立讨论规范和相互了解都是对课堂时间的宝贵利用。当一个班级成为一个社区时,每个人都会学到更多,创新、试验并加倍努力倾听彼此的意见,提出重要的后续问题并多听一些,可以为包容提供所需的机构支持。
Hazel Rose Markus是戴维斯-布拉克行为科学教授,斯坦福SPARQ的联合创始人 和联合主任, 也是《冲突 !如何在多元文化世界中茁壮成长。

辩论工具
通过 黛布拉萨茨
大学校园内思想自由交流的许多挑战来自外部:有些个人和组织会监督持有有争议观点的教授的教学,有些团体只是想煽动对抗,我们的公共文化充满了希望关闭或淹没理性审议的声音。互联网的存在也意味着我们许多出于善意的错误可能会传播开来,所有这些社会力量都会导致诚实、探究和艰难的讨论变得令人不寒而栗。
但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来自内部。让我指出我们课堂上可能出现的自由探究的三个障碍:
墨守成规。在我们的课堂上言论自由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自我审查。许多学生害怕发表与他们认为是同龄人的主流意见相悖的意见。的确,当所有收到的意见似乎都与自己的判断相悖时,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屈服于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所称的“习俗的专制主义”,追随多数人的观点,参与集体思考,或者至少保持沉默,要容易得多。
主观主义。一些学生得出结论,在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意味着道德价值观是主观的——它们只不过是意见而已。如果那是对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讨论和推理它们了,但那是不对的。我们可以通过查看它们是否与我们持有的其他价值观和信念一致来使我们的价值观受到压力;考虑到可行性限制和事实,我们可以提高对成本和权衡的认识;我们可以用其他思维方式来面对我们的想法,看看它们是否经得起严格的审查。
教条主义。一些学生从分歧的存在中得出结论,肯定有人错了,但并非所有的分歧都是不合理的。真诚的人有动力寻找共同点,并查看相同的证据,但仍然会对政策产生不同意见,因为他们对此类政策中涉及的道德价值观赋予不同的权重,或者因为证据不完整且难以解释,或者因为他们评估不同结果的风险不同。
我们可以用其他思维方式来面对我们的想法,看看它们是否能生存下来。
我们有教学工具来解决课堂上的这些困难。苏格拉底的方法也许是哲学产生的最好的东西,苏格拉底相信将一个人的信念置于反例和批判性问题的压力之下的方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从正义是“真理和所取之物的回报”的日常观点开始,并论证这种观点会导致矛盾。通过质疑持这种观点的人,苏格拉底表明他那个时代的常识性道德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施加压力来解决这些紧张。面对批判性质疑和公开询问,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和对正义的信念。
魔鬼代言人是另一个有用的工具。当观点——包括珍视的观点——不受挑战时,教育机会就失去了,当相反的观点是错误的或不合理的时,情况甚至可能如此。正如John Stuart Mill所写,“只要战场上没有敌人,老师和学生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睡觉。” 对于教师来说,以不同的视角来模拟参与是很重要的,在我的民主思想课上,我总是肯定会教授对民主最强烈的批评,并在必要时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
目前,我们正在重新考虑我们的本科课程,以便在大一的课程中让学生反思他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考虑在多元化和自由的环境中持续存在分歧的事实。社会,认识到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性,并塑造文明和相互尊重的规范。愿我们在斯坦福的努力取得成功,并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Debra Satz是Vernon R. and Lysbeth Warren Anderson人文科学学院院长,也是Marta Sutton Weeks社会伦理学教授。
本站是提供个人分享的知识,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人观点。如有侵权,请告知!